
王德威,知名学者,在华语文学研究界影响力颇大。毕业于台湾大学外文系,曾任教于台湾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现任哈佛大学东亚系暨比较文学系讲座教授。代表作有《被压抑的现代性:晚清小说新论》《想象中国的方法:历史·小说·叙事》《抒情传统与中国现代性》《当代小说二十家》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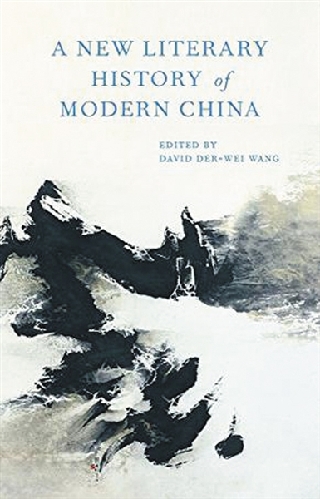
A New Literary History of Modern China(《哈佛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
作者:王德威
版本:哈佛大学出版社 2017年4月
最近,由腾讯文化、京东图书、中国人民大学联合主办的“21大学生世界华语文学人物盛典”在京举办,首位致敬对象为哈佛大学东亚系暨比较文学系讲座教授王德威。典礼活动上,王德威发表的演讲题为“‘华夷风’——华语文学的视界”。
虽然王德威自2006年起就开始论述“华语语系文学”这个概念,但对于大多数读者和听众而言,它依然显得陌生和辽远。他以“华语语系文学”的概念替代旧有的“海外文学”“华侨文学”“汉语文学”等称谓,来呈现复杂、多生、不同文化互动的华语文学面貌。这也许是惟有身在海外的研究者才可能具备的开阔视野。
从《被压抑的现代性》中谈到的“没有晚清,何来五四”,到《抒情传统与中国现代性》中对中国文学“有情”历史的召唤和重新叩问,再到现在的“华语语系文学”,王德威的研究从来不缺少批评和争议,但又总能以新的理论构架、新的诠释方式带来明确的启发。新京报记者对王德威教授进行了专访,他以一贯的谦和、有礼和自信,讲述了他眼中的文学、文学研究和文学史。
“华语语系文学”
我们需要更丰富、更复杂的文学世界观
新京报:你是怎么开始对“华语语系文学”这个命题有了研究的兴趣?
王德威:“华语语系文学”的前身是我们一般所谓的海外文学,或者是广义的世界文学、华文文学、汉语文学等,这些命名基本是在中国的学制语境中给海外文学做出的定位。在国外教了很多年的书以后,总觉得这些定义不能够穷尽我们在海外对于自身所生活的,或者所面临的各种文学现象的一个比较丰富或者复杂的陈述。所以大概是在2006年、2007年,在美国加州洛杉矶大学任教的史书美教授提出了“Sinophone Literature”(华语语系文学)的观点,我对这个新的论述方向很有同感,并愿意就她所提出来的论述再加以发挥。我在中文语境里可能有更多的发声机会,就用“华语语系”这四个字,与过去的海外文学、华侨文学、汉语文学这些五花八门的命名来做一个区隔。毕竟我们做文学的需要一个新的品牌、新的命名,来作为进入这样一种新的文学世界观的方法。
新京报:和华语语系文学相对的可能是我们传统的这个“中国文学”的概念,它的出现本身就内在于中国近现代化这样一个过程,有一种民族意识的东西在里面。所以当使用“华语语系文学”这个概念,是不是也包含了对民族意识这方面的反思?
王德威:对,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写作机制和它所论述的方式,的确是跟民族国家的想象与论述息息相关。我们所习惯的这种国家文学史,它的历史也不过就是一百多年。我无意去质疑或推翻这样一个命题,它已经是历史存在的现象,既然大家都认为这是一个约定俗成的文学史的写作方式,我觉得言之成理,这不是问题的所在。问题是怎么去面对国家文学史所不能够照顾到的各个层面的、仍然使用华语创作的、或者是发生的这些现象、这些文化的场域。
在过去用“海外”这样的词难免有一个预设,有海外就有海内。另外像“世界中文文学”,这个“世界”也是很暧昧的一个词,讲“世界中文文学”的时候其实是不包括中国的,但世界明明已经是世界了,为什么中国又可以在世界之外来为这个世界命名?所以这里面就有高下主从的一个分别。我们倒不是在谈论文学市场或者文学世界里面阶级斗争的关系,而是“华语语系文学”是不是能够提供一个不同的批判界面,作为我们研究中国文学的时候,一个另外的对话的对象,或者是一个思考的维度。
海外中国学的影响
年轻学者不会再人云亦云
新京报:在文学领域,所谓的海外中国文学往往是处在一种被边缘化的处境中,但在学术研究界,海外中国学的研究却是对中国本土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和差别?
王德威:这个我没有一个明确的答案。海外文学研究在方法跟理论模式上对中国本地的学者产生了很多影响,但我们这群所谓的海外学者也没有那么了不起,因为我们的很多方法也不过是将西学的用到中国的这样一个转手的运用而已,在那个意义上我们甚至可能就像是一个掮客,是做二手传播的。
我想这可能还牵涉了广义的中西学术论述的一个不平等模式。我有最常用的一个论述:你现在穿的一身衣服其实是西式的,但你每天没有掏心撕肺都在想我穿着西式的衣服,想我对不起祖国吧?我们没有为服装的问题或是手机、电视的问题而这么紧张,那为什么在文学这一块就往往成为大家争论的焦点?这反证了文学、学术这一块在中国的文明想象力中占据的位置,大家觉得这是我们的核心,不能够被拿走,不能被掏空。我认为历史就是这样发生,那就承认它,我们不需要再有任何的借口或解释,我们更应该关心的是我们如何来改变。
新京报:那如何来改变呢?有可能改变吗?
王德威:也许下一步是我们怎么样来发展以中文语境为基准的一个论述模式。希望有一天,也许在10年或20年以后,我在美国的比较文学系,我会告诉我在英美或是法国或德国文学有成就的理论学者,说你如果不知道朱光潜的理论,你也太落伍了吧;你如果不知道李泽厚的理论,你也太落伍了吧;你如果不知道胡风的左翼理论,你可能也太落伍了。我觉得这是一个交流的过程,当然我会觉得我有很自觉的一个承担、一个责任。
在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里面,大家逐渐已经比较平静。交通如此快速,年轻的一代学者阅读能量这么好,可能不需要什么欧美学者来教导我们怎么样。相比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出国留学的那一代,我想年轻一代应该会有更多的自觉,不会再人云亦云。
重写现代文学史
发生论本身是不得不存在的一种神话
新京报:今年是2017年,是被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发端的1917年“文学革命”的百年纪念。你曾提出“没有晚清,何来五四”,今年又新出版《哈佛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在这本新作中你怎样处理中国现代文学发端这个问题?
王德威:这本新作是由161篇短文章合在一起的文学史。其中第一篇文章,我刻意用了三个时间来说明现代中国文学是怎么发生的。第一个时间是1635年,当时一个晚明的文人叫杨廷筠,因为受到了西方耶稣会传教士的影响,给文学做了一个审美的、西方模式化的定义,所以这是一个遥远的所谓文学现代发生的开端。这篇文章又给了另外两个日期,一个是1932年,一个是1934年。1932年是周作人对于“新文学源流”的一个探讨,1934年来自于河南的左翼史学家嵇文甫,他们不约而同地都把晚明当做是现代中国性的开端,尤其是文学方面。所以我刻意用三个时间点来说明,这个发生论本身是不得不存在的一种神话,我们不断去发明这个神话。
新京报:你对这几年中国文学或者说华语文学的创作有一个怎么样的观点?或者说有哪些作品给你留下最深的印象?
王德威:我觉得现在的作家,也许他们生存的时代不是一个最能够造星的时代,所以我们现在还没有看到像上世纪80年代所谓新时期作家一出来的那种一个时代的整合的爆发力。
但我特别要讲,我认为华语这一块是在中国语境之内被忽略的。我觉得过去的20年到30年,华语世界文学的成绩是绝对值得注意的。我们现在大约只有白先勇在中国国内是华语世界公认的一个代表性人物。但是我觉得在八十年代末期以后的这二三十年里面,不论是香港的董启章,或台湾的骆以军,还有之后的吴明益、甘耀明这些作家,以及马来西亚华人中的一批作家……他们汇集出来了这样的一个广义的华语世界,我觉得作为中国内地的读者,或是批评者和创作者,似乎应该把眼界扩大。当然我们的能力跟智慧都有限,但至少在世界观上,应该是把这些作家他们的创作都纳入考虑范围,或阅读的可能书单之内。这是我最大的期望。
采写/记者 李妍

-
“炫父”大赛:一起晒出心中的Superman
2017-06-18 13:49:04
-
国家相册《百年话剧魂》丨《茶馆》为何能成话剧经典?
2017-06-18 13:49:04
-
下个月起,这样做可以抵扣个税!你能省多少钱?
2017-06-18 13:48:25
-
下半年,你的五险一金将迎来5大喜讯!
2017-06-18 13:48:25
-
这些老百姓厌恶的不正之风,国家“零容忍”!
2017-06-18 13:48:25










